欧亿体育官网-比利时与斯洛伐克战平结束
发布时间:2025-02-25编辑:admin阅读(44)
谢凌洁比利时与斯洛伐克战平结束,笔名凌洁,浔桥。广西北海人。居比利时安特卫普,以写作和中文教学为业。曾在北海金融部门工作,1999年辞职。2001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发表在《十月》《花城》《中国作家》《大家》等期刊,部分被《小说选刊》等转载,有作品入选《中国女性文学》等几种选本。曾获广西青年文学奖,华侨华人文学“中山杯”新人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辫子》、散文集《藏书,书藏》和长篇小说《双桅船》等。
走过欧亚大陆两岸(一)
◎谢凌洁
离开国内之前,我回到北海两年。这两年里,我和谁最亲?和侨港一帮侨民最亲,和哪里最亲?和承载这些侨民的侨港最亲。以致面临告别这个陪伴我多年的侨民小镇时,我有深深的惆怅和眷恋,甚至抱歉。在那相当漫长又相当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日复一日的本能,便是到侨港去,看她去,拍照去——以致至今我独有两张存满照片的碟子、里面全是侨港的照片。晨曦中的侨港,黄昏里的侨港,季风中的侨港,台风里的侨港……
至今,我依然难以理解自己缘何对一处渔港的眷恋不舍到比利时与斯洛伐克战平结束了那样的程度,因为那不过是地理上的一处地方,而不是一个人,因而你也许认为我对小镇的这种眷恋不是一种感情,而只是一种情绪。我只能和你说,当你有同样的遭遇时,你方感同身受。我正是因为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她给了我陪伴和安抚。我和她的关系,一如和那些我经历过快乐幸福或磨难的地方,需要三番五次地回去,谁也不见,独自发发呆就能解决些许悲伤郁结。

其实,美丽时尚的北海才是我曾经生活的城市,我和北海的关系是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11年的朝夕相处,世纪末我辞职别了小城,6年的辗转流徙之后再回去,我们成了彼此的叛徒,谁也不认识谁了。那是父亲的弥留之际,儿子正青春炸放,我甚至没有冲动和心力去寻找一个曾经的故人说说我的酸涩,而直接,我就向同样作为“外来者”的侨港投怀送抱,奔向她的芜杂和动荡,乃至浪漫。
曾经离开北海前,我在这里知识不少侨民朋友,这次回来,我重新又回到他欧亿体育官网们当中,从他们那里知识更多,感受更多。他们的人生是被嫁接的,仿似一棵从他乡移植回来的大树,庞杂的须根却似乎永远地留在他乡了,不少人想奋力寻回自己的根基,却是徒劳。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的祖辈都葬在印度支那的土地上,按照祖先葬在哪里,哪里是故乡的逻辑,他们的故乡不在这里,尤其是,不少家庭的亲人在印度支那的疆土上去了前线,民主解放战争、统一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弥漫不断的硝烟,让众多的家庭支离破碎,如今到了中国都已经几十年了,人不见回来,尸骨也不见。从1991年中国和越南恢复建交之后,不少人便长期往返在中国和越南的寻亲路上,活见人死见尸的逻辑和信念支持着他们的道途,他们只求得自己的亲人回来——不管他们的亲人是死是活,免得他们年年节节总在餐桌上多摆一双碗筷,多做几个粽子糍粑。
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难民小镇是悲怆的,沧桑的,然而,这种沧桑并没弥盖她的风情和迷人。它虽然不大,和北海不到半个小时公车的距离,但生活完全是别样格调,落后,脏乱,芜杂,纷繁,又有种未知的神秘和诡异,街市小摊小店的热闹温馨,港湾渔船挤堆的局促动荡,于我,都是种好奇。一两条街道的小镇,可说弹丸之地,可哪怕只有一个“越南卷粉”摊上,便看见北海咫尺之遥的此处补丁般的难民地,他们随带而来的,不仅仅是他们曾经的流徙动荡,而是伴随他们动荡人生的异族文化和历史渊源。比如,卷分摊上作为佐料的薄荷和洋葱片,在那时我便确定这种文化绝非来自中南半岛的安南,而必定和印度支那的宗主国法兰西文化渊源相关。果然,这在我到了欧洲生活后,确认这个事实。我所在的比国乃至欧洲,薄荷和洋葱同样是日常必备佐料,尤其洋葱,被作为不少人家的蔬菜食用(注:因气候差异,这里吃洋葱,不觉体内产生奇臭气体)。而我所在的比国,近200年前同样是法兰西帝国疆界,如今我所在的安市中心的皇宫里还有拿破仑三世的行宫。这是后话。
其实,从2001到2008的8年期间,我不曾中断到侨港去。哪怕在北京在南宁的几年,只要回到北海,牵引我心魂脚步的,还是侨港。因而,那些年我和这里不少侨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经历的种种都会和我说,有的有种种不满,甚至受到种种不公和非难,他们会找到我,让我帮他们到政府去说,然而,一个无权无钱的码字者,能做到什么呢。在这点上,我是对侨民一直抱愧的。但心里的信念倒不曾放弃,我知道会尽自己努力的,我始终会为他们做点什么的,以我一个写作人的方式。
在等待欧洲签证直至上鲁院之前那段时间,我非常期待到最近距离的口岸上住一段,好好看看这个港口,和那些长年累日飘荡在海上的侨民的生活。其实,以往我偶有接到侨民的邀请出海甚至远航等等,但我天生怕水,这种惧怕源于个人的经历。一是小时候在竹林盐场的储水田里溺水几近夭折,其二是成年后有过两次几近跳海的经历,一次是1999年夏季坐客轮到涠洲遇风浪晕眩虚软,一次从涠洲岛坐渔船去斜阳岛,在几十海里漫漫海路上,看浪涛汹涌烟水浩淼几近失去抵抗的耐力。然而,对海上生活我总是好奇的,尤其是对这些烙着战争印记的难民,对他们的生活不仅好奇,更多了悲悯。总觉得他们的背影,要比一程公车之外的北海人要沉重得多,他们的生存背景,和那一池“黑墨”的港口之间有着一种宿命般的纠缠,这种被叫做“苦难”的东西,甚至在不短的时期里,还直接地困扰了我。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更深切地看到一些东西,一些导致侨民这种处境的更深层的原因——这些深层的原因在我到了欧洲读了大量的历史之后明悟,这同样是后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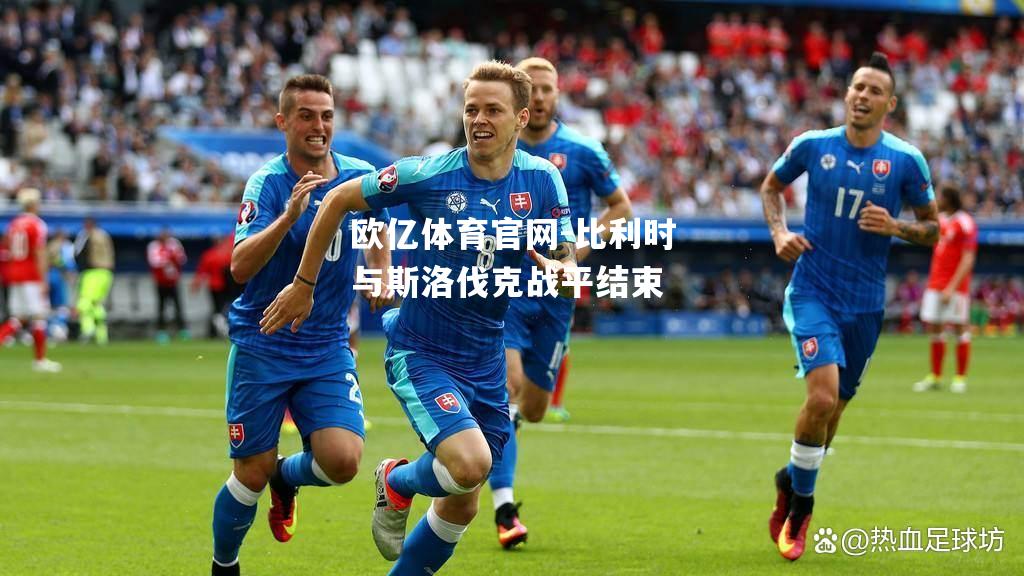
彼时,我知道,那一池“黑墨”的港口里,那些葡萄架一般排排串起灯泡、晒衣绳上挂着长短汗衫和胸罩裤衩的木头渔船,和那些敞怀露胸穿着短裤汗衫、吆喝着摸麻将抽水烟筒的渔人,他们的种种不会因为我的告别而从我的大脑中消失,反将会和我往后的生活如影随形。
明白了这个必然,我决定在辞别前到港口呆一段,听听她的呼吸心跳。
通过侨港镇政府的人,很快被告知可住到港口派出所民警值班的办公室里去。港口的派出所办公室就在港湾岸上,离水一米有余。房间不大,但很洁净,我每次到来,必带上自己的床褥。里面的人对我们很好,很照顾,从不打扰。我和陈媛把沙发搬出屋檐下,伸脚可触到海岸。夜幕中,渔港漆黑一片,搭乘渔人进出的电动渡船,时时叫嚣,犁得水浪一浪浪地涌动,那泊在湾里的老旧或废弃的船艇也随着浪峰在我们脚下来回涌动。在很多个夜里,我们几近不睡,就那样坐在窗前的岸上,看夜幕中渔船来往移动的黑影,听渡船哒哒叫嚣的窘迫和急切。(未完待续)
●本文欢迎转发,谢绝擅自转载、盗用图文